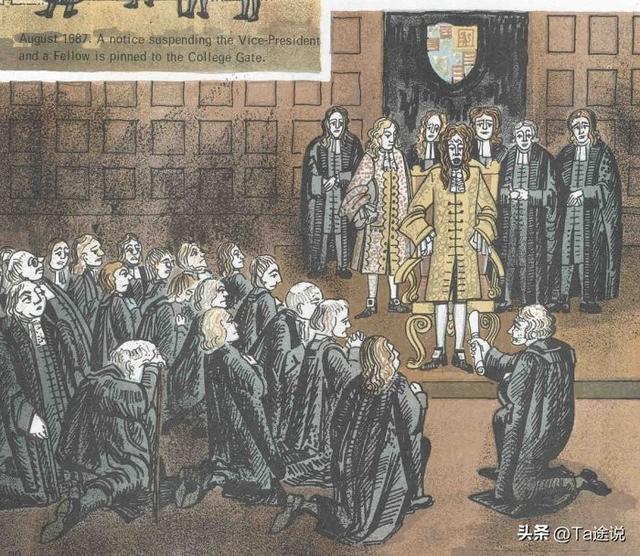虽然议会通常是请愿者请求的主要存放处,但另一种重要且独特的订阅形式是向中央政府部门和部长的请愿书,通常称为纪念馆。商人、制造商和其他部门团体纪念政府的做法从十七世纪开始就已经确立。
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各地建立了地方商会,“主要是为了游说政府的经济政策”。这些机构的永久成立使纪念馆制度化,成为商业游说团体与政府互动的主要机制。
例如,在1821年至1889年间,曼彻斯特商会向政府发送了233个纪念碑,这些纪念馆大多涉及对外贸易、关税以及国内和国际邮政服务,并写给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外交部和邮政总长,但也写给大法官,当他们涉及破产法或有限责任时。
通过纪念馆进行游说往往是有效的,在曼彻斯特商会于1868年纪念邮政总长之后,该镇的收集和交付数量迅速增加。纪念馆通常通过国会议员的媒介转发,充当当地经济利益的守护者,利物浦议会办公室成立于1812年,港口的商人通过他们的国会议员向政府发送了纪念碑。
在此期间,他们包括乔治·坎宁和威廉·赫斯基森等内阁部长,他们经常支持这些要求,赫斯基森在转发一份纪念碑时写道,“不可能不让相当大的重量”纪念馆的抱怨,他们“包括所有银行家和许多第一批经纪人和商人”。
在1850年代中期,布拉德福德商会发现,尽管有自己的议会代理人,但如果纪念馆通过当地代表的渠道,政府更愿意“满足他们的要求”。当然,商业游说团体向议会发送了有关影响他们感知利益的立法或税收的请愿书,例如理查德·阿克赖特的专利在1785年提出续签时,以及王室,例如1782年西印度种植园主和商人的情况,然而,部门利益集团经常发现,与这些其他类型的请愿相比,纪念馆享有某些优势。
作者认为,与向下议院请愿不同,纪念馆不受议会先例的限制:它们可以打印,可以包含额外的文件,并且不需要真实的个人签名,这意味着姓名可以远程添加到打印文件中,而无需本地化的签名收集过程,这是公众请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论是否通过国会议员转发,纪念馆及其求职信都为纪念馆成员提供了直接向部长发表讲话并与他们展开对话的机会。例如,1842年,伯明翰商会利用四个纪念碑与总理罗伯特·皮尔爵士就货币问题进行辩论。
纪念馆是私人或半私人文件,在政府和那些商业游说团体之间提供了一条特权的沟通途径,这些游说团体通常反对从不断扩大的政治抗议和公共竞选活动中部署策略。十八世纪末,一些激进的商人,如曼彻斯特棉花商人托马斯·沃克试图使用更大,更普遍签署的公开请愿书,结果证明是有问题的,有争议的,效果较差。
当压力团体或其他政治运动,如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反传染病法案鼓动使用他们自己的纪念碑时,他们倾向于将它们更多地视为公共文本,广泛传播和出版,就像公众请愿一样,对于部门团体来说,纪念馆作为私人的、谨慎的诉求权威比作为公共文件更有用。
虽然向议会的公开请愿通常是简短的,但纪念馆通常是冗长而密集的文件,作为备忘录,1837年,为了纪念内政大臣约翰·罗素勋爵,曼彻斯特改革者对规范工厂工作的立法运作中的技术缺陷提出了长达六页的详细批评。
纪念者有说服力的诉求基于证据、兴趣和专业知识,而不是像议会请愿书那样,以签名数量、援引公众舆论或主张权利和正义为依据。压力团体在公共问题上的纪念馆往往强调纪念馆的专业知识。
1880年代,废除《传染病法》的活动家纪念自由党总理威廉·格莱斯顿,将签署者归类为宗教牧师,神职人员,军官和医生。因此,纪念馆是压力和利益集团向政府展示其专业知识的方式之一,偶尔也向更广泛的公众展示,预示着二十世纪与非政府组织相关的专业知识政治的兴起。
作者认为,与请愿书相比,纪念馆在其他两个方面增加了优势,这两个方面都强调了它们对于发展和维持与精英政治家的联系和接触的重要性。与公开请愿者不同,纪念者更期望他们的纪念碑会被政府考虑,即使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他们也会收到回应。
利物浦议会办公室的信件包含公务员和部长对纪念碑的回应,确认收到并说明已提交给有关部门。彼得·朱普在对十九世纪早期政府的研究中观察到,“财政部的六个部门和单一的贸易委员会每周大约开会两次,审议涉及金融和商业各个方面的大量纪念馆,请愿书和调查”。
更重要的是,纪念馆是面对面游说的名片,因为它们可以在书面文本之外进行政治代表和官方交流,虽然当局普遍抵制请愿者要求出庭权的要求,包括1842年的宪章主义者,但受宠的纪念者似乎享有代表权的特权,通常由当地国会议员陪同。
当肯特农业学家在1838年反对政府取消对外国水果的进口关税时,他们在他们的纪念碑之后向贸易委员会派出了代表。伯明翰商人在1847年游说首相约翰·罗素勋爵进行货币改革时使用了类似的策略,曼彻斯特商人在1858年墨西哥内战期间向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勋爵施压,命令海军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
1888年,联合商会纪念政府,并派出一个代表团游说支持美国和英国之间贸易争端的仲裁,然而,追悼会成员不享有代表权,他们的接纳似乎主要由有关部长自行决定。部长们不太热衷于看到代表压力团体或群众政治运动的代表,而不是提出具体、有限要求的地方或经济利益集团,规范工作时间的工厂运动广泛使用了纪念馆和代表,这表明这种做法可以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被工人阶级活动家使用,而不仅仅是商业游说团体。
然而,更典型的是,总理本杰明·迪斯雷利在1880年拒绝接受妇女参政论者的代表,理由是其他企业的压力承认了他们的纪念碑。纪念馆演变成一种独特的请愿形式,为商会和其他部门利益集团提供了特殊的可能性,事实上,纪念馆可以被视为实践的共同根源,这些实践随后多样化并专门化为现代内部商业游说政府。
通过纪念馆和代表,纪念馆和政府为利益集团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协商建立了日益正规化的渠道。这些进程和程序并没有损害国家来之不易的无私声誉,但确实为政府提供了有关具体或技术问题的宝贵信息,并有助于将新的社会和经济行为者纳入既定的政治结构。
作者认为,向君主请愿,是十八世纪臣民表达对汉诺威王朝、既定的教会和国家机构以及新教忠诚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与革命和拿破仑法国的战争期间。即使在表达改革派或激进主义意见时,对王室的讲话“通常比向议会请愿更具赞美和奉承性”。
请愿的风格深受收件人性别的影响,对国王的称呼通常以家长式的术语来指代他们的收件人,布拉德福德居民致威廉四世的讲话,赞成在工厂工作十小时,“最谦卑地呼吁陛下,作为你们人民的父亲,干预您的宪法权威,并将您的皇家保护盾牌投向穷人的孩子”。
1837年维多利亚登基后,请愿者,尤其是女性,用母性修辞称呼女王,就像反奴隶制和反谷物法的演说一样。作为例行公事,地方议会、教堂和社团向王室发送请愿,庆祝或同情王室的出生、婚姻、死亡和加冕典礼,一些有进取心的牛皮纸商人在这些场合积极推广地址,渴望从订阅城镇和城市获得业务。
然而,这样的讲话并没有脱离更广泛的政治,1803年,达勒姆的公司在最近的一次暗杀企图后致乔治三世的讲话中表示“祝贺天意发现并防止了针对您庄严的人的晚期叛徒图谋以及国家的稳定”。虽然这些讲话往往表示忠诚并赞同政治现状,但它们可能成为表达更多颠覆性意见的工具,许多激进分子和改革者在1820年向乔治四世疏远的妻子卡罗琳女王发送了支持他的地址,当时国王试图与她离婚。
向女王发表讲话,为对政治制度的广泛批评提供了宪法上无可挑剔的掩护,在共和主义是一种边缘观点的政治文化中,流行的君主制是整个政治光谱中普遍持有的信念。因此,包括激进派、极端保守党和妇女参政论者在内的非常不同的团体将君主视为比他们认为腐败、非法或不具代表性的议会或政府更高的权力。
这些团体呼吁君主以臣民的名义批准改革、反对立法、解散议会或解散政府,1829年,极端保守党议员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试图阻止给予天主教徒公民权利,敦促其他人“煽动国家:不是请愿,而是向国王提出解散”。向君主讲话使请愿者避免承认议会或政府的权威或合法性,并确实呼吁国王对这些其他政府部门行使至高无上的地位。
作者认为,请愿者可能会在议会策略的同时解决君主问题,而不是作为议会策略的替代方案,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一贫如洗的伦敦造船工人向王室和议会提出了双重请求,其逻辑是前者会鼓励后者对他们的担忧采取行动。
对君主的纪念、演说和请愿书可以作为文件提交给国会议员,当他们考虑对相关业务采取行动时。通过立法程序支持一项措施意味着请愿者依次向下议院、上议院和君主请愿,在不同的权力和不同风格之间切换。
因此,在上议院无视他们要求跟随下议院于1831年10月通过议会改革的请愿书后,曼彻斯特居民向威廉四世提出干预并采取“决定性的宪法手段”将这项措施纳入法规。对君主的讲话数量及其签名没有系统地记录下来,但零星的参考资料表明,这是一种常规做法,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激增,表达忠诚的演说通常发表在《伦敦公报》上,事实上,在某些场合,该杂志几乎没有其他内容。
在整个十九世纪,也有来自寻求个人冤情的个人致君主的请愿,在1850年代,维多利亚州每年收到约800份此类请愿书。当群众运动试图动员他们的支持时,这可能会导致大量针对君主的签名。1842年,来自妇女的500多份反谷物法演讲被发送到维多利亚州,其中包含超过50万个签名。
1851年,愤怒的新教徒将英国重建罗马天主教等级制度称为“教皇侵略”,并提出了3145个请愿,包含超过一百万个签名,呼吁女王作为圣公会的领袖和新教信仰的捍卫者。向王室请愿的演变揭示了君主制宪法地位的重要转变。1689年的权利法案保障臣民向君主请愿的权利,并允许请愿者要求接触皇室听众,这是大众君主制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事实上,未来的王室刺客往往是沮丧的请愿者,坚持他们有权亲自向君主示威,然而,1840年代对维多利亚的多次暗杀企图导致立法禁止这种个人接触君主。在此之前,请愿者可能会亲自接近君主,要求贵族和国会议员在宫廷的社会活动中发表演讲,或通过内政大臣的媒介发送请愿书,一些特权机构,如新教异议代表,保留了亲自向君主提交地址的权利,但大多数请愿者被指示通过内政大臣将地址发送给维多利亚。
实际上,大多数地址似乎只限于内政部,内政部选择了应该通知皇家私人秘书的地址;其余的人得到了礼貌的、不承诺的承认。最初作为一种安全措施和行政便利的东西在十九世纪末获得了制宪会议的地位,为保护王室免受政治影响提供了防火墙,1893年,当统一党议员桑德森上校计划从阿尔斯特提交一份反对爱尔兰地方自治的请愿书时,皇家私人秘书亨利·庞森比爵士向他讲述了为什么这在宪法上是不可能的:
女王不能在她负责的顾问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任何政治请愿书或演说,除非有他们的建议,否则她也不能答复任何此类呼吁。我想,如果你描述的这样的演说是私下提交给女王陛下的,那将是违宪的,请愿书的意思当然是,女王应该解雇她现在的自由党大臣,你会明白,如果没有一些负责任的顾问出席,女王陛下不可能听这样的演讲。
爱德华时代的妇女参政论者以某种公正的方式抱怨说,向王室请愿必须由内政大臣而不是请愿者亲自提出的惯例违背了他们作为1689年权利法案规定的臣民的自由。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请愿者作为这一领域的主体的权利被重新配置,作为对君主制宪法地位的更广泛重新定义的一部分,君主制与党政府和代议机构越来越疏远。正如妇女参政论者所承认的那样,向君主请愿可能会产生有价值的宣传,但请愿者并不幻想君主会对政府的其他部门行使更高的权力。
出处:
英国地方治理中的民意表达机制 李济时
17世纪英国中下层妇女请愿活动探析. 张弢
论公民请愿自由. 章志远
表达与监督:英国的议会请愿制度. 左一彤;李红勃
《英国议会政治》. 诺顿
《英国政治制度史》. 阎照祥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kuaisuzugao.com/8443.html